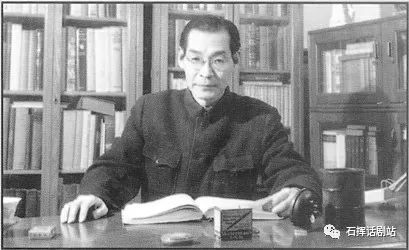


斯氏认为演员创造出的“具有独特性格的人物形象”是从哪里来的?人物的外部形体特征是从哪里来的?斯氏的“种子论”中的人物形象的“种子”又是从哪里来的?“种子”到底是来自演员自身内部呢,还是来自外部?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以及完成演员创造的途径又是什么?焦菊隐的“心象说”与这些课题又应怎样做比较?
一、斯氏的理念
斯氏一生探索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开掘具有演员天赋(气质)的年轻演员的作为人的(心灵的、形体的、言语的)天性”,从具有表演天赋的演员本人的身心中创造出性格形象来。斯氏提出,首先要发现未来形象的性格核心——“种子”,再由此生发出形象。斯氏早期认为,“种子”存在于演员的心灵内部;后来斯氏提出,既要到演员的心灵内部去寻找,也要到作家的剧本中去寻找。这就是“角色,是作家笔下的人物与演员的身心相结合的产物”的内涵。
从认识论和反映论层面说,斯氏认为生活是艺术的创作源泉。但是从方法论层面说,斯氏不赞成演员创作的舞台形象应该到生活中去寻找,更不赞同到生活中进行摹拟,也不同意未来舞台形象的性格“种子”是来源于生活的。
斯氏的“种子”与“从自我出发”学说是互相联系的整体。从创作方法与过程上说,演员“从自我出发”了以后,跟着就要运用“种子”学说,然后获得形象的“内、外部自我感觉”,经过从“有意识”到“下意识”的排练,从演员的身心生长出“形象”这棵大树。如此创造而来的角色,既是“角色”,又是“演员”。

二、焦菊隐的学说
焦菊隐早期不反对“从自我出发”,这从他的理论文章中看得出来,但后期提出“从生活出发”,实际上是把“从自我出发”否定了,而且他也不完全同意斯氏的“种子论”的学说。焦菊隐的办法确实比斯氏的更容易把握,他认为舞台形象的“源泉”也存在于生活当中,表演创作方法也是到生活中去寻找“形象的原型”,于是提出“从生活出发”,然而,生活中却没有哪个现成的人就是剧本中虚构的人物,所以还要综合“剧本中的描述”、“生活中的原型”、“演员自己的特点”对形象进行捕捉、培育、创造。将“剧本”、“生活”、“演员”这三种因素捏合在一起以后,还需要有一个“构思”过程,由演员完成的构思,最终还要形成人物的“心象”,经过演员的反复揣摩与不断练习,让“心象”逐渐“化”到演员身上去,最终使“心象”成为舞台上的“形象”。
三、两者辨析以及由此引起的思索 焦菊隐的“从生活出发”的核心是对“生活原型”的摹拟,斯氏的“从自我出发”是把自己的体验奉献给角色,以获得“自己的”,然后是“人物的内、外部自我感觉”;焦菊隐的“心象说”需要演员在心里“看”见角色,斯氏的“从自我出发”及“种子论”则要靠演员与角色的高度“合一”。
古里叶夫说,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在心里创造出来的,是经过了构思的,它首先是一个心中的“形象”,然后才是一个欣赏者看得见的“艺术形象”,因此艺术作品中的人叫做“形象”。焦菊隐的从“心象”到“形象”的学说,符合一切艺术的基本创作规律。
焦菊隐的无比清晰、明了的有关“构思”的学说,为什么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却不使用呢?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演员艺术是所有艺术当中唯一创作者自己既作为材料,又是未来的创作成品的艺术,当艺术家认识到了创作材料当中还包括着创作者的情感,也就认识到了在进行创作时,很难像其它艺术的创作者,“站在材料的对面进行创造”,而应该把自己“投入”进去进行创造。

斯氏远赴法国学习时,“理想的范本”学说问世已近六十年了(狄德罗在其中提出“理想的范本”命题的《演员是非谈》问世于1830年前后,斯氏诞生于1863年,去法国学习表演时大约二十五岁。),斯氏只要运用这一学说的合理部分,去掉其中认为演员在表演中“应该避免情感投入”的不合理的部分,就能简明扼要地像焦菊隐那样去解释演员创造角色的全部创作心理过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难道斯氏一直没有发现过演员创作也有“构思”,也会形成构思中的“内心形象”吗?不。已发现的资料证明,不是这样的。在斯氏未发表的手稿中,有以下关于“性格化”的文字:
“大家知道,有些演员在想象中给自己创造出规定情境并使其达到尽致入微的程度。他们在内心看到他们想象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一切。
“但也有一种有创造性的演员,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们身外的事物,不是环境和规定情境,而是处在相应的环境和规定情境中的他们所扮演的形象。他们在自己身外看到它,注视着它,同时在外表上抄袭这个想象出来的形象所做的动作。
“还有一些演员,他们所创造的想象中的形象对他们说来已成为他们的 alter ego,他们的孪生弟兄,他们的第二个‘我’。它不停不休地同他们在一起生活,他们也不(与它)分离。演员经常注视着它,但不是为了要在外表上抄袭,而是因为处在它的魔力、权力之下,他这样或那样地动作,也是由于他跟那个在自己身外创造的形象过着同一的生活。有些演员对这种创作状态抱着神秘的态度,准备从似乎在自己身外创造出来的形象中,看到自己的非尘世的或轻飘飘的身体相似的东西。
“如果说抄袭外部的、在自己身外创造的形象是一种单纯的摹仿、摹拟、表现,那么,演员与形象共同的、相互而紧密地联系着的生活就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过程,是某些具备创造性的演员所固有的……(原稿中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郑雪来译,第三卷,注释,55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北京。)
中国学者常将斯氏这段未发表的文字与焦菊隐“心象”学说联系起来,试图证明“心象”说是对斯氏体系的继承,是对斯氏未完成的“性格化”塑造方法的实践。引述在先后顺序上也常常(也许是在无意之间)把斯氏的这段文字,放在斯氏一生几个重要学术成就之后,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时间上的感觉:这是斯氏晚年的思考。
但是,史实与这类叙述有出入。斯氏有关“性格化”的这一部分未发表的档案手稿的卷首,清楚地标明了手稿写作的时间:“1933年春”。(详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郑雪来译,第三卷,注释,55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北京。)我们知道,《演员自我修养》写成后先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于1936年,然后斯氏于1937年对部分章节进行补充,俄文版出版于1938年。(《演员自我修养》俄文版的内容是由斯氏确定的,但是斯氏本人并没有见到该书的正式出版。)但是,这些版本的正文中都没有这一部分斯氏手稿中的内容。
从1933年到1938年的五年时间里,斯氏都不认为手稿中的这一部分内容能够代表他对“性格化”问题的思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斯氏从来没有带领学生按照手稿中的内容进行过表演训练。可以说,我们一直以来读到的《演员自我修养》中的内容,就是斯氏最新的有关“性格化”方法的发现,而手稿中的内容则是斯氏早就已经超越了的旧的观念。
我国学者“文革”后几次讨论斯氏在“性格化”上的“不足”,常常拿出“理想的范本”、“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心象”等学说来,试图以这些学说来弥补斯氏的“性格化”的“不足”。“理想的范本”的学说与斯氏早期手稿中“孪生弟兄”确实非常接近。不过,“理想的范本”的学说比斯氏的年纪还要大三十多岁,等到俄文版的《演员自我修养》问世时,“理想的范本”的学说问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仅从时间上看,斯氏在《演员自我修养》中发表的论述也是最新的观念与最新的有关“性格化”塑造的研究成果。
斯氏的“性格化”学说相当新,新到它从问世至今已经近八十年了,某些学者还没有弄懂它的核心观念与学术价值。

直到斯氏“从自我出发”奔向角色“性格化”的方法问世以前,所有老的“性格化”方法所追求的是“像”,因为一直以来属于这一源流的演员们都认为舞台上的性格形象存在于“外部”,也就是存在于演员身体与心灵以外的某个或某几个地方,需要通过演员的“摹拟”才能获得。一百年前是摹拟老一辈演员的表演,七十年前是摹拟生活中有特点的人,近五十年来是摹拟根据生活中无数有特点的人加上演员的自身条件综合而成的内心形象,即“心象”。
焦菊隐的“心象”说比“理想的范本”前进了一大步,对当年没有多少创作经验的演员来说,这一套方法非常好用。但是这毕竟不完全是斯氏的方法,斯氏方法中的核心部分,“从演员的身心中生发出形象”的理念,从两个方面被替换掉了:“形象来自于演员自身内部”的认识,被悄悄替换成了“形象来自于可以被我们摹拟的外部”;于是,“从自我出发”被悄悄替换成了“从生活出发”。这其实是用一个正确的“认识论”层面的表述,替代了同样正确的“方法论”层面的表述,其实质是否定了斯氏“方法论”的核心内涵。
斯氏的传人,当年在中戏任教的鲍·格·库里涅夫专家不同意在表演训练的启蒙阶段,让那些初学表演的、年轻的,还没有把他们本人在行动中的心理过程梳理清楚的学生们,从外部去摹拟观察对象的“外部性格特征”。专家认为,以这样的做法进行表演启蒙训练是有害的。
从库里涅夫的教学记录中可以看到,专家带领学生做观察生活作业时,是让学生以自己的身份边讲边演,但是并不要求把“演”的部分再让学生化身成“观察对象”,以“摹拟”作为训练目的,再把它“演”出来。库里涅夫的训练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梳理生活的逻辑、行动的逻辑和人的逻辑,以更好地完成表演诸元素的训练。(笔者曾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向俄罗斯彼得堡国立戏剧学院的谢·得·切列卡斯基教授进行询问,所得到的回答与本段落的表述大致相同。)
斯氏体系是完整的创作与教学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最高任务”与“贯穿动作”的学说,“真实感与信念”的学说,“从自我出发”的学说,“种子论”学说,通过“有意识”的技术达到“下意识”创作的学说,“从自我出发奔向性格形象”的学说等。
最高任务与贯穿动作不仅要求演出的思想性,而且也要求演员在创造人物时首先接近人物的思想与感情,它是思想性的要求,也是创作方法的要求;真实感与舞台真实,既是“体系”所要达到的美学目标,也是体系的方法论内容;“从自我出发”、“种子”论以及从“有意识”达到“下意识”,则是“体系”的方法论内容。
发现了演员表演创作天性的规律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对演员“摹拟形象”,反对“摹拟生活”,也反对演员摹拟在脑海中创造出的“内心形象”,因此他不让演员到生活中寻找“种子”,也不允许寻找创作过程中的“内心形象”。
上述斯氏反对的方法,在斯氏诞生以前的欧洲表演大师与理论家那里,都已经实践过了,而且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但也正因为这些方法存在弊端,让斯氏开始了新的探索。也许正因如此,斯氏在推崇“从内到外”的方法时,显得有些固执,对“从外到内”的方法,又显得非常谨慎,甚至是过于谨慎。
创作的“方法与途径”不同,形象的“来源”不同,所产生的剧场艺术的审美效果也就会不同。那些从演员的身心直接产生的形象常常真实得让观众“信以为真”,其影响深入人心,挥之不去,这正是真正的体验艺术的伟大之处与魅力所在;那些融入了从外部摹拟的手段所产生的形象,常常真实得让观众“叹其真像”,这又是融入了“表现派”手法的表演艺术的精湛之处。
深入探究,两者确实有着不一样的美学品格。我们的话剧工作者与观众见到的更多的是后一种,而对于前一种,多见于书本,由于多年来没有见过多少优秀的演出,更没有见过来自俄罗斯的演出,终于失去信念,开始另创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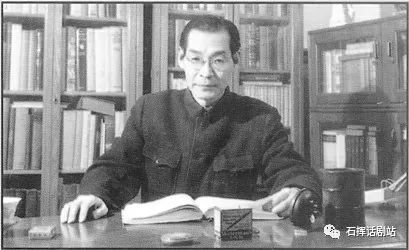
然而,斯氏对表演艺术的伟大贡献正在于其“性格化”道路与以往所有的“性格化”道路都不相同。斯氏是先从演员的身心内部找到形象的“性格种子”,经由导演的帮助,将之培植成“性格形象”的。因为“形象”已经是从演员身上“长”出来的,所以他(指角色)已不存在“像”与“不像”的问题了。因此斯氏学派总是强调:形象既是剧中的角色,又是演员,是二者的“合一”。
为什么斯氏的“性格化”方法总是受到怀疑者们的否定?斯氏到底要不要“性格化”塑造呢?斯氏“性格化”方法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斯氏是追求“性格化”塑造的,“体系”的方法也可以塑造出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体系”的最终目的也正是要塑造出性格形象。斯氏本人,还有克尼碧尔、莫斯克文、梅耶荷德、查哈瓦等都是塑造出了性格形象的伟大演员。
莫斯科艺术剧院赴欧美演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演员们塑造出了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莫斯克文和克尼碧尔在《沙皇费多尔》中扮演了沙皇与皇后,等到观众们观看另一台戏《在底层》时,竟没有看出正是他俩扮演了路加与妓女;到了观看《樱桃园》时,又没有看出他俩扮演的是叶比霍多夫管家与庄园主朗涅夫斯卡娅。可见,斯氏和他的合作者们创造的舞台艺术从未被人指责缺乏鲜明的性格特征。
问题可能在于,斯氏用他自己的方法塑造出了性格,而别人运用他的方法却没有塑造出性格。在没有塑造出性格的不成功的学习者当中又分两种,一种是斯氏的学生的学生在传授中把他的体系教条化了,使之僵死了;还有一种是学习时间相对较短,其实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践中的真传,多数人主要仍是靠读斯氏的书来实践其原理的,这其中还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抱有怀疑的态度,自然也就更难学会,然后,越学不会就越产生更多的怀疑。
伟大而质朴的艺术最难学习,没有才能的人甚至永远也学不会。斯氏体系是为了创造伟大的表演艺术而存在的。斯氏的“性格化”品味更高、更难实现,而一旦实现了也就具有更加感人至深的力量。今天,俄罗斯的表演教师和导演在“从自我出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有时在创作之初不给演员剧本,也不说要排什么戏,而且根据剧中的情境与人物关系让演员以自己的经历做练习,让演员把自己情感世界完全奉献给角色。俄罗斯戏剧教师曾对我说,这正是斯氏晚年实验过的方法,这与任何模拟内心形象的方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斯氏说过,“体系”是俄国人的“体系”,也是适合表达俄国人情感方式的“体系”,所有外国学习者可以从中发现对自己民族有用的东西,但是由于民族性格与民族生活内容的不同,绝对不可照抄斯氏体系。
焦菊隐在创造民族戏剧的过程中,没有简单地照抄斯氏理论,也没有让他的演员简单地摹拟“心象”,他在自己的“心象”学说中,加入在反复练习的基础上将“心象”渐渐“化”到演员身上的创作环节。正是在这个环节中,焦菊隐又将“从自我出发”与“第一自我”、“第二自我”的学说结合了起来,这是焦菊隐的重大贡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我们总是急于“创新”,虽然拜了斯氏及传承者为师,却又没有耐心像美国人那样认认真真,傻傻乎乎地跟着外国师傅一学就是十几年。我们是太过聪明的民族,我们总是刚“学”了没多久就想“创新求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这两大剧院,在1954年以后都以学习斯氏体系为自己的学习目标与美学旗帜,也算是都认了斯氏这个洋师傅吧。但是北京人艺在学习中把“从自我出发”换成了“从生活出发”,在获得人物“内、外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捕捉“心象”;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走得更远,在不断升温的学习斯氏体系的热潮中还做出了如《张家小店》那样的表演作业,由一个人扮演所有的人物,其间有进入人物的“行动”,也有跳出人物的“说表”,这样进行创作当然没有问题,甚至应该赞扬,但是以此当作学习斯氏体系的成果,就说不过去了吧。
美国戏剧家从1925年开始学习斯氏体系的创作与教学方法,中国人从1937年开始学习斯氏体系,七八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美国人创立的承自斯氏体系的“方法派”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在世界戏剧各大演剧流派林立局面中占一席之地。反观我们的现状,虽然也有北京与上海两大剧院各自打出了具有特色的演剧学派旗帜,但实际上我们的戏剧舞台后继乏人,我们年轻演员的表演水平与年轻演员的成长令人忧虑,这些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体系”,我们并不是踏踏实实学了十年甚至是二十年以后再来断定我们是不是确实不适合学,或需加以发展与改进,或改弦更张,我们是刚一学就“变招”了的。第一代学习者“变招”就快,下一代人“变招”就更快了。
今天,在俄罗斯“体系”学派的传人当中,在美国李·斯特拉斯伯格的“方法派”传人当中不断有表演艺术家,甚至是大师级艺术家涌现,而我们在培养新人上虽然也有成绩,但和这两个国家相比差距又比较明显。“文革”过后,当我们重新学习“体系”时,一股世界范围内的“结合”、“借鉴”、“创新”之风已吹到了中国剧坛,但对基础性创作课题的研学任务却并没有完成。
不把基础性问题及主要创作方法学深、学透、学扎实、学到手,就很难出现持续不断的高水平的结合、借鉴与创新。即使一时间创造了绚烂的舞台艺术,也终究难以将这个局面保持下去。我们应该抓住今天中国戏剧教育界及演出团体同俄罗斯等国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大好时机,扎扎实实地对戏剧艺术的基础性创作课题来一次深入探究与回炉淬火,为在下一个戏剧百年里取得更扎实的进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2024-10-16 14:36:39
2024-10-16 14:35:51
2024-10-15 10:14:13
2024-10-15 10:12:30
2024-10-15 10:09:31
2024-10-15 10:08:10
2024-09-09 15:23:57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