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文章来源于石挥话剧站
作者Dionysus1

“观演关系”是指由导演在演出艺术处理中创造并把握的,存在于观演空间内部的审美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相互刺激、交流,共同并且同步创造出剧场艺术的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说它特殊,是由于表演艺术具有创作者、创作材料和创作成品都是演员本身这样一种特性。其它艺术作品当它没有欣赏者的时候,艺术作品本身还是存在的,而演出艺术就不同了。演员艺术是由活人扮演角色的艺术,具有一次性特点,演出必须有人观看,否则就不是演出而是排演。没有了欣赏者,演剧艺术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舞台演出就不能回避观众的存在,就不能不考虑怎样建立起观演双方相互交流的关系并始终把握主动权,使演出既能引起观众兴趣、促成观众对演出的热情参与,又使演出的艺术完整性不因观众的参与而被打断、甚至是遭到破坏。

在观演关系诸问题中,首要的是演员与角色的关系,即确定解决演员与角色的矛盾的方法,确定以什么样的演剧观来实现舞台演出;第二是考虑如何在剧场里引导观众参与戏剧演出,确定观众的参与应属于哪一种性质。比如是偏重于心理参与,随着演员的表演去体验角色的情感,还是在心理参与的同时再伴以行为上的参与——与演员正面接触、直接交流等等。正是“由于演员和观众是主要的戏剧因素,对两者间关系的处理便是导演艺术的首要问题,”(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43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观演关系的处理,反过来又对全剧总的处理原则的确立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演出的总体原则包括演出的体裁、风格、艺术特色的解释和处理以及演剧观念的确立。‘演剧观念’在导演构思中涉及的主要是演员与角色的关系和舞台与观众席的这两对关系的确立和处理。这两组关系的确立,基本上决定了一台戏的表演方法和使用舞台的原则,决定着舞台形象的性质和演出形式。”(同上,86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观演关系的处理对于导演创造一台成功的舞台演出的重要意义。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如何处理观众参与问题,是创造、处理观演关系的中心环节。
(二)
现在,我们来对演出史上几种最具代表性的观众参与的阶段性现象作一个简要回顾。人类最早的戏剧演出,今天已不可能得到较完整的形象资料和文字记载了。但是戏剧史学家在探讨戏剧的起源时仍然对最初的戏剧演出作过一些推测,其中一种认为戏剧起源于原始人的簧火晚会。当一个原始人向其它同伴讲起他获得猎物的经过并邀请一个同伴来假扮猎物、共同将打猎过程模仿一遍的时候,就产生了戏剧及其观演关系的萌芽。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演出”的话,那么不难想象观看者的参与一定是热烈而积极的。因为猎物的获得关系到每一个氏族成员的生存,同时因为这种观演活动本身还具有祈求上仓赐予猎物的原始宗教意义,因此“观众”对于“表演”也就不会是漠不关心的。在这种原始表演中,虽然可以大致分出演员与观众这两方,但是双方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观看者可以提问,表演者可以根据提问来进行表演,回答问题。因此在这种早期的“演出”中,观众的参与是全面的,观演双方不仅在心理上,甚至在观演场地,以至于在观演双方的各自身份上也是相互交融的。当表演的一方和观看的一方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时,戏剧也就随之诞生了。
更多的学者认为,戏剧起源于祭酒神和宗教唱诗活动。当唱诗队中分化出了第一个演员时,戏剧也就诞生了。据说古希腊悲剧就是如此衍生的。有关古希腊的戏剧演出我们就有资料可循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戏剧演出,其观演关系是相当活跃的。因为演出时间长,有时一个戏要演好几天,观众一般都带着食物入场。“戏不动人,大家就吃吃喝喝;名演员一出场,大家就把饮食收起来,聚精会神地观看。戏演到好处,观众叫好、鼓掌、要求重演……遇到拙劣的表演,观众就叫倒好,……用无花果打击演员,甚至用石头打击……观众甚至要求更换节目,演下一出剧。……喜剧诗人可以使剧中人物和观众开玩笑……或是向观众扔水果和麦饼。”(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可见在古希腊戏剧演出中观众不仅参与演出,而且这种参与还大大超出了剧情本身。因为在古希腊,戏剧演出常常是节日庆典的大的社会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演出中虽有观众与演员之分,但在总体的意义上,在庆典这个大的社会活动中大家都是参与者,是特殊的“演员”。这也是古希腊早期戏剧演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

中世纪宗教演出的“观演关系”和古希腊有相似之处,也是大型活动的一部分。但演出内容转向宣讲宗教故事。“大型的宗教演出,演员与工作人员往往要上千人。中世纪的城镇原来不大,演员业余参加,这几乎使每家每户都与演出有关。……当戏演到耶酥在迪拿一家穷人家里参加婚礼,按照《圣经》故事,清水要变成香酒,面包还会成百倍地长出来,许多观众都来分饮香酒和分食面包,观众与演员一起参加了迪拿的婚礼,亲眼目睹耶酥奇迹的发生。”(吴光耀:《西方演剧史稿论》74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我们看到,与古希腊的观众参与不同的是,中世纪演出的观众参与不仅是对演出做出心理上和行为上的反应,而且还在行为上参与到剧情中间,如去领酒和面包。在某些瞬间,观众与演员溶合为一个整体,虔诚地站到了上帝面前。此时,“上帝”成了整个宗教活动的唯一的“观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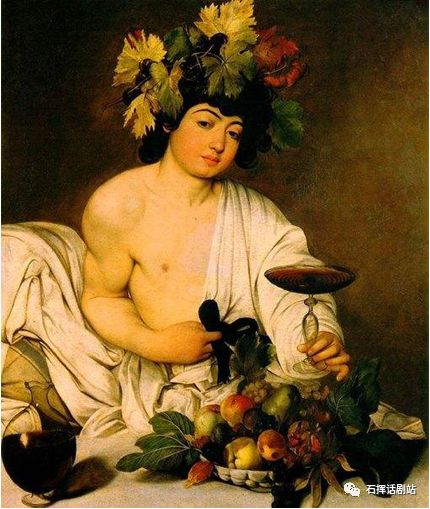
今天某些导演试图尝试通过自己的演出处理使这种观演关系复活。然而自从那个哲学“疯子”喊出“上帝已经死了”,自从人们渐渐没有了中世纪的那种宗教热情,果真还能产生那样的“演出”吗?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舞台大多是伸出式的,观众从四面观看,演出没有布景。剧场观剧区域的大部分也没有顶蓬。大多数观众都是站着看戏的。观众来自各个阶层,包括小商人、学徒、工匠等。(参见王佐良《莎土比亚绪论》36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当时的大多数剧本都是作者为特定的剧团而写的,比如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从他的剧本中可以看出许多台词是直接说给观众听的,同台对手应听不到。观演双方无疑存在着直接交流的现象,很象是戏曲里的“背躬”。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比英国要来得早。在意大利先是出现了镜框式舞台的雏形,渐渐地在全欧洲都出现了今天我们常见的镜框式舞台。舞台与观众席被分割开来,观众的参与开始逐渐变得具有更多的心理和情感的性质。至此,“第四堵墙”的理论就快要出现了。
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的安托万于1877年组建了自由剧团,(以前常说成是“自由剧院”,其实,那时他们还没有固定的剧场,所以叫“自由剧团”更为合适。)提出了“生活的截面”和“讽刺性喜剧”的自然主义戏剧主张,上演了托尔斯泰,易卜生等人的作品。法国的让·柔琏在安托万的自由剧团建团的同年就提出:“演员要表演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去理会观众的反应,任他鼓掌也好,反感也好,舞台前沿应该是一道第四堵墙,它对观众是透明的,对演员来说是不透明的。”(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100页。)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第四堵墙”理论的出现。这种演剧观念的逐渐流行,使得舞台被完全封闭起来,使观众能够更深入体味到角色的内心情感。运用这种演剧观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长期的演出与教学实践中,创立了“体系”,创立并发展了心理现实主义演剧学派。
在幻觉主义美学观滥觞的同时,戏剧创作领域也并存着非幻觉主义的美学观念。稍后,当写实在舞台演出随着现实主义的发展成为舞台上的主流,就有了梅那荷德、皮斯卡托、布莱希特等人强烈地感到了“第四堵墙”的桎梏,他们通过大量的反幻觉主义观念指导下的实践推倒了这堵“墙”,创立了新的演出形式及其观演关系。
中国出现这样的革新要比欧洲晚了将近四十年,但却进展神速,在新时期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尝遍了幻觉主义戏剧舞台上的“禁果”。
(三)
上个世纪的新时期,中国戏剧导演的创作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创造性地打破了单一的演剧观念,在演出形式上进行了大量探索,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一时间,在假定性的旗帜下,出现了一批打破第四堵墙的演出。同时赞美假定性的文章也屡见不鲜。一些文章甚至对于封闭式的舞台处理和再现的美学原则的演出颇多微词。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1988年10月上演了美国剧作家赫尔曼的《哗变》。

该剧楔子为美国海军凯恩号扫雷舰在航行中遇上了十二级台风,舰长魁克在风暴中指挥有误,副舰长玛瑞克受人纵容,强行接管了魁克的指挥权,指挥战舰驶出了风暴圈,事后,魁克向军事法庭控告玛瑞克犯有哗变罪。戏,就从这里开始。演出展现了法庭审讯的全过程,演出处理也是按照再现的原则实施的。如果要在《哗变》的演出中作一些打乱时空顺序,心理空间外化这样的处理,这个剧本可是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能性的。但是导演并没有做这种处理。难道是导演对观演关系问题没有考虑吗?当然不是。
童道明在《〈哗变〉的成功》一文中相当准确的道出了来自美国的赫斯顿导演对该剧的观演关系的艺术处理。“每个证人在证人席上的作证,都是被严格局限了的舞台时空中的充满矛盾的心理运动,都是一个能产生种种意外的但又绝对合情合理的戏剧情境”。……“朴实无华的导演手法使观众很快领会了这出戏的艺术语汇,知道了要欣赏《哗变》就得静下心来听捕捉台词中的潜台词,观众也很快当真领略到了倾听的乐趣、语言的魅力,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听到的要比舞台上的审判官们听到的更多。”(童道明:《戏剧笔记》6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版。)通过再现原则的处理,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对人物语言的潜在含义上来,使观众听出话外之意、弦外之音,细细地品味人物的心理活动,看透每一个登场人物的深藏在行动之中的行为动机,乃是导演对于该剧观演关系处理的着意追求。观演过程中观众几乎没有发生过行为上的参与,但观众在心理参与上的程度之深,恐怕是同时期上演的其它演出都难以比较的。
在观演关系问题上,本来就存在着“封闭式参与”和“开放式参与”这两种形式。只偏重前一种势必造成演出形式的单一。但是,刚刚从单一的演出模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导演,又实在没有必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让“新形式”和“新手法”成为“新的桎桔”。导演创作者们也没有必要仅从演出的外部形式上对优秀的演出进行模仿。创作的枷锁早已打开,不同的观演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魅力。优秀的戏剧演出最终带给观众的,不是某一种形式本身,而是通过准确的形式所揭示出的形象与思想。
(四)
到了上个世纪末舞台上重视观演关系处理的演出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着意于打破观演双方的界限,并且希望造成观众看戏过程中身临其境的心理感受。还有一些尝试不仅想要造成观众的行为参与,甚至试图将观众拉入到戏剧情境之中,使观众也成为情境中的一个角色。
导演们进行这种尝试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一个就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波兰导演格罗托夫斯基后期实验的影响。格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曾尝试取消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界限,甚至干脆将演出称之为“聚合”。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大约五百人,参加他组织的不分创作者和作品,不分演员和观众的“平行戏剧艺术”。按照格氏的设想,这些人一起到森林里去渡过一个昼夜,体验一次内容包括火、气、土、水、吃食、跳舞、游戏、种植和洗澡等宗教仪式的活动。格氏认为参加者可以在纯宗教仪式中重新发现戏剧的起源,也可以使参加者真正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吴光耀:《西方演剧史论稿》75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难怪有人认为格氏后期的活动已不属于戏剧实验范畴,而应看作是人类文化学方面的研究。
上个世纪末国内导演的某些迫使观众进入戏剧情境的作法,其目的与性质与格氏的实验不尽相同,但从观演关系的角度来看,都是试图打破观演双方的界限。可是在演出中,这种作法常常使某些观众感到尴尬。在西方也同样有观众因不满类似处理而提出抗议的例子。
吴光耀对这类现象的批评是:“追求观众直接参与,是镜框式舞台长期分隔演员与观众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然过头了,效果不一定好。事实上有些观众被卷人进去以后,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戒备性抵触,他们反而感到自己受到愚弄,演员与观众的隔膜远没有消除,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出现而已。”
演员与观众本来就有着天然的界限。在剧场空间里,在演员与观众中间也一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界线”。这条线从戏剧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它的存在,在原始宗教活动中,正是因为出现了“观”的一方和“演”的一方,才从宗教活动的母体中诞生出了戏剧。
应该看到,无论观演双方的物理距离是远还是近,也无论是早期的开放式剧场还是近代的镜框式舞台,这条“线”都是一直悄悄地存在着的。近代镜框式舞台与“第四堵墙”理论的出现,使得这条线变得更加清晰了,但终究是那条“线”的存在,引起了“墙”的出现,而不是因为有了“墙”的出现,才有了那条“线”。如果,硬是要在演出中取消这条“线”,进而取消演员与观众的区别,其结果不是这种演出损害了戏剧,就是反过来由戏剧将这种演出抛弃。

因为,一旦彻底消灭了观演双方的界限与本质区别,也就再也不存在任何观演双方的“关系”了,戏剧,或许,也就由此消失……
2024-10-16 14:36:39
2024-10-16 14:35:51
2024-10-15 10:14:13
2024-10-15 10:12:30
2024-10-15 10:09:31
2024-10-15 10:08:10
2024-09-09 15:23:57
 ×
×
 ×
×